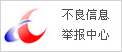順天街的舊時光
作家王躍文說:“人是不可能走出故鄉的,哪怕他走過萬水千山。”我深以為然。
故鄉順天那條短小簡陋的街道,長不過幾百米,卻一直沒走出我的腦海,那人,那事,常常在夜深人靜時跳出來。它見證著歲月的更迭與人間煙火,承載著代代順天人的記憶與情感。
街頭是順天大橋,街尾是順天中學,大橋過去三四里路就是我的家,那條街是我初中上學的必經之路。晚飯后,同學們三三兩兩穿過街道溜達到順天大橋,那是一種輕松愉悅的節奏。我們常常倚著橋欄,看橋下潺潺的流水和咿呀劃過的漁船,看天上無憂無慮的云霞和兩岸綠油油的莊稼,一天學習帶來的疲勞便煙消云散,眼里洋溢著飛揚的青春和無限的憧憬。那時的橋比現在單薄,橋面不寬,橋墩數量少,結構輕巧,來往的車輛也少。在我們眼中,這橋不僅是交通要道,它更宛如一處靈動的天地,是我們漫步散心、駐足凝望的獨特風景之所在。
這條老街的鮮活,多半藏在圩日里。每逢農歷一日、四日、七日是順天圩日,趕集的人們成群結隊從各家出發,有人帶著農作物、家禽家畜出售,有人來買生產生活用品,街上人流如潮。廣播里放著上世紀80年代的歌曲,吆喝聲、叫賣聲、討價還價聲此起彼伏,熱鬧得很。圩日的中午,我總不愛在學校午休,總愛到街上逛逛,盼著遇見趕集的父母,討點零花錢買小食,或是看看他們有沒有捎來魚仔干、河蝦之類的葷菜。哪怕沒什么事,單是沉浸在圩日的熱鬧里,感受那份濃郁的生活氣息,就覺得滿心歡喜。
年晚圩更是把這份熱鬧推到了極致。作為農歷臘月最后一個圩日,它是一年中交易最活躍的一天。村里人半夜就提著燈火、挑著蘿卜青菜去街上占攤,豬肉、糖果、年畫、對聯等年貨擺滿街巷,忙活了一年的人們,終于能放下農活,為過年添置家當。那天的順天街,家家戶戶男女老少都趕來了,熟人碰面熱情打招呼,人群擠得密不透風。我侄子阿鋒三四歲那年,我哥帶他趕年晚圩,一轉眼孩子就不見了。家人發動所有趕集的熟人找遍了每個攤檔,從中午找到下午三四點,我哥這個七尺漢子急得眼眶發紅,全家人都揪著心。好在有驚無險,侄子哭著喊“爸爸”往沙溪搭凹的村口走,恰好遇上我姐姐的朋友琴姐。琴姐認出孩子,抱著他趕回街上,這場虛驚,成了我對年晚圩最難忘的記憶。
老街的煙火氣,也藏在一個個鮮活的人身上。順天街有兩位開店鋪的李老板,大家稱他們“大李”“李仔”。大李個子不高、微胖,待人總帶著笑,村里人都樂意和他交易;李仔是他堂弟,精瘦,臉上布著小黑痣,話少不茍言笑。李仔是父親的老熟人,父親喊他“李哥”,每次趕集都要去他店里喝茶聊天,買些菜種、咸魚豆豉之類的東西。李仔挑著雜貨擔走村串巷時,也常來我家歇腳,我最愛買他的麥芽糖,他總會用興寧客家話念叨著“打多點,打多點哈”,用小鐵鑿敲出一大塊給我。父親也總用好酒好菜招待他。只是每次父親在李仔店里給我買鞋,都只挑姜黃色的男款鞋。我疑心他店里只順帶賣男鞋,更不懂父親為何執意如此,每次抗議,父親都板著臉說:“小孩子的鞋分什么男女?能穿就行!”他生氣的樣子很嚇人,我不敢反駁,只能穿著男鞋出門,被小伙伴起哄時,恨不得把鞋扔掉。那些鞋從沒穿爛過,都是我偷偷割爛、扯爛的。我寧愿趿著姐姐的舊鞋,也不愿穿這些不合心意的男鞋。
村里的“阿狗”,也是圩日里繞不開的人物。他和父親年紀相同,我喊他“狗爺”,他皮膚白凈、高高瘦瘦,總在街上閑逛,村里人說他有“第三只手”。那時我不懂這話的意思,只知道他眼疾手快:蹲在煙絲攤卷支煙的工夫,就能順走夠抽三四天的煙絲;從雞鴨攤走過,轉眼就能從懷里掏出幾只小雞小鴨。有人打趣說他會“遁術”。他靠這些小動作混日子,也有失手被打得半死的時候,村里人總拿他當反面教材告誡孩子,卻也并不真的討厭他,反倒覺得他是老街的一樁“趣聞”。
也是在這條街上,我第一次真切體會到生活的不易。大學畢業那年暑假,我和父母各挑著兩籮筐花生到街上賣,他們交代好價格便回家干活,留我守著攤位。整擔買每斤1.5元,散買1.8至2元,這是父親定的價。直到中午,才有個商販模樣的男人來詢價,他翻了翻籮筐底下的花生,嘗了嘗干濕,還價到1.2元,我搖了頭,他便走了。此后零星有人問價,卻都沒成交。到下午三點多,趕集的人散得差不多了,那個男人又回來,只肯出8角一斤,還說“不賣你就得擔回去”。我咬咬牙答應了,最后只賣了150元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一路哭,這些花生是我和六十多歲的父母鋤地、挑肥、除草、收摘換來的,那么辛苦,只換來這點錢,我終于懂了勞動的艱辛,懂了父母掙錢有多難。
如今再想起順天街的舊時光,那些熱鬧的圩日、鮮活的人、酸澀又溫暖的小事,都成了我心底最珍貴的寶藏。這小小的街道,早已成了我的精神家園,無論走多遠,都走不出它的溫柔牽絆。
作者:朱宏球
熱點圖片
- 頭條新聞
- 新聞推薦
最新專題

- 強國必先強教,強教必先強師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國第41個教師節,主題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,譜寫教育強國建設華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