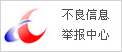滿簍秋光茶油香
油鍋“滋”的一聲,我倒進母親捎來的今年新榨的山茶油。香氣升騰而起時,我仿佛看見她在晨光里緩緩直起身,望一眼擁群山入懷的萬綠湖,又低下頭,繼續把枝頭的油茶果一顆顆摘下。又是一年山茶油飄香的時節,窗外的風里,像是裹挾著一縷熟悉的香氣,清冽而醇厚,像一根極細的絲線,不經意地,便將我的心從這片鋼筋水泥的叢林,牽回了那萬綠湖邊的土磚灰瓦屋,牽回了那漫山遍野的山油茶香氣里。
那土磚灰瓦屋,依偎在萬綠湖臂彎里的龍溪村。那時的湖,還不叫萬綠湖這個詩意的名字,我們都叫它新豐江。湖水是終年碧綠的,像一塊巨大溫潤的翡翠,靜靜地臥在群山環抱之中。山是層林疊翠的,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畫,最挨近湖水的是墨綠,而后是翠綠,再往遠處去,便成了含著煙嵐的淡綠。而在那個秋高氣爽的時節,最惹人注目的,卻是那漫山遍野的古油茶樹,山茶果由青轉紅,果皮微咧,油脂含量達到峰值,正是采摘最佳時機。然而春天的時候,山茶樹不開艷麗的花,只是默默地將一朵朵象牙白的花藏在綠葉叢中,可它的果實卻沉甸甸地壓彎了秋天的枝頭。
記憶里,采摘油茶果的時候天還未大亮,母親便喚我起身與其做伴。上山的路上,露水很重,母親總走在前面,她的解放鞋不一會兒就洇濕了。肩上挑著竹簍,竹簍里放著蛇皮袋,那簍子隨著她的步子,有節奏地輕輕晃著,與扁擔摩擦發出咿咿咿的聲響。她的背影,在晨霧里顯得格外清瘦,卻又有著一種說不出的韌勁。山路兩旁的草葉上,都綴滿了晶瑩的露珠,在微光里閃爍,我樂在其中。
母親看見哪兒有果實累累的油茶樹便鉆進去,她的眼中溢出了油茶香。仿佛那香氣,是綠色茶果殼略帶青澀的苦味,是咧開棕色果仁里蘊藏著的油脂的芳香,是林間泥土與草木的氣息,它們混合在一起,撲面而來,沁人心脾。母親是采摘油茶果的好手。她的動作是那么嫻熟,從不用蠻力去拉扯,只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油茶果的根部,輕輕一擰,便聽見“啪”的一聲脆響,油茶果就干脆利落地掉進了竹簍。當陽光越過山脊,從高大松林的枝葉間篩下來,落在母親因常年勞作而粗糙的手指上,那些光斑就在她摘油茶果的動作間跳躍成金色的弧線。
她偶爾會抬起頭,用手肘上的衣服擦一擦額角的汗珠,望一望遠處的萬綠湖,眼神里便有了片刻的悠遠;她也會絮絮叨叨地跟我叨起她小時候跟著外婆去摘油茶果的事,那些瑣碎的舊話里,滿是懷念——比如哪一年的油茶果結得最好,榨出的油是怎樣個香法……這些絮叨,與林間的鳥鳴聲、風聲混作一體,聽起來溫柔而安詳。那時的我,還不太懂得這些話語里的深情,只顧著在密集草叢里尋覓掉下來的軟糯香甜的野柿子和椎栗。
不一會兒母親的竹簍里的油茶果漸漸堆成了小山,紅的、青的,沉甸甸地壓著竹簍,也壓著母親眼角的笑意。她直起身,用粗糙的手掌輕輕拍了拍果堆,指尖劃過果皮上的白霜,像撫摸著自家的孩子,嘴角彎出的弧度里,滿是藏不住的滿足——這是一年的收成,是罐子里清亮的油,是我們餐桌上的香。她讓我扯開蛇皮袋口,把竹簍的山茶果倒進去。日頭升到半空時,母親把蛇皮袋口扎緊,牢牢系在扁擔上,往肩上一放,順手扶住兩頭的繩子,邁開步子便往山下走。我提著裝有野柿子和椎栗的竹簍,跟著母親下山,期待母親回家把椎栗用柴火炒熟。山路依舊彎彎,她的腰彎得更沉了,解放鞋踩在落葉上發出的沙沙的聲響,扁擔與繩子的咿呀聲,比來時更顯厚重,卻一步一步,走得穩穩當當。
如今,我離那湖,那山,那油茶樹已是山一重水一程。城里的超市貨架上擺著各式各樣標簽精美的茶油,可我總覺得,它們少了那一味草木與泥土的香——那是在晨露里浸潤過的,被母親的手指溫柔撫摸過的,被萬綠湖的清風吹拂過的魂……
油鍋的滋響漸漸平息,茶油的香氣卻在鼻尖久久縈繞,不肯散去。這香氣,從來都不是油的味道,是母親晨霧里的背影,是萬綠湖不變的碧色,是童年山徑上的野柿甜與椎栗香,是母親藏在歲月里,從未走遠的溫柔牽掛。
作者:黃貴美
熱點圖片
- 頭條新聞
- 新聞推薦
最新專題

- 強國必先強教,強教必先強師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國第41個教師節,主題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,譜寫教育強國建設華章”。